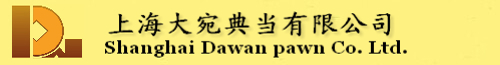老上海典当行你知多少?
2014-07-14 18:10:58 点击:
老上海典当行你知多少?在老上海人的印象中,说起典当,很容易条件反射联想起一个名词:“万恶的旧社会”。有一出沪剧叫《为奴隶的母亲》,说的就是可恶的“典当”——典妻的故事。拿女人作“典当”,这还不够万恶吗!家喻户晓的“白毛女”的悲惨故事,讲述的也是恶霸地主黄世仁逼佃农女儿喜儿以身体典她父亲杨白劳的所谓欠债。后来我在电影和连环画上只要看到墙壁上那个足有一人多高的硕大的繁体字“当”,我就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我们习惯叫它当铺,看到它,总感到旁边那扇黑森森的门洞里藏着陷阱,只要你一踏入,就会遭遇灭顶之灾。至于里面那高高的柜台,以及在柜台上只露出大半个戴着瓜皮帽的脑袋,加上那透过老花镜上方射向典当者的狐疑的目光,都会让人不寒而栗,感到典当者来到这里,显然是挨宰来了。问题是即使挨宰,典当者也只能来。对后者来说,跑典当行就是跑生活。典当者已经只剩下典当一条生路,一旦失去这条生路,生活就面临绝路。
今天,历史已经进入了新世纪。昔日的典当行已经远了。走近我们的已然是全新意义上的典当业。据此前沪上一家报纸报道,全国规模最大的典当行在沪开张,宣称汽车、房产皆可质钱,还将从事股票质押贷款。果然,这样的典当行开张后,一些投资者、生意人、房产商看中其比银行更便捷的时效,纷纷向它“调头寸”,把资产转化为资金用于再投资。以至有识者指出,以前一直是“穷人的后门”的当铺,如今已然成了一个特殊的金融机构。但是尽管如此,看到那个硕大的繁体“当”字,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已经远去的老上海当铺。尤其是当我在梳理有关旧上海社会舞台上曾经出现的一幕幕场景时,那个触目惊心的繁体“当”字更是时时回闪在眼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记述他对旧上海的印象时说,“上海虽为世界第一流的城市,在墙壁上以丈尺大字写出的商业标识不是雪佛兰轿车或奇异GE电气用品,而是当铺之‘当’与酱园之‘酱’。”在我看来,这个“当”字分明也是历史对现实的一种提醒,提醒今天,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幕。
好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全家曾去已故著名作家茅盾的家乡桐乡乌镇旅游,当时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的陆泱在旅游参观景点之一的乌镇老当铺时,居然足足逗留了老半天,他一会儿坐上高高的典当柜后面那把高凳,目光透过眼前那扇小窗,望着游人出出进进;一会儿又跳下来,颇感新鲜地在八仙桌旁的大扶手椅上坐坐,我猜测儿子对这里的印象一定觉得非常好玩。他对历史的阅读和了解还很有限,还体会不到那时的穷人挟着典当物战战兢兢走近当铺,会是一种什么心境;还不懂得探究在这些前来当铺的穷人家里正发生着什么。
近代上海的典当业是相当兴盛的。说中国典当业的存在已有几千年历史决不为过。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曾引述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中的记载说,16世纪中国有当铺两万家,至19世纪仍有七千家,所以黄仁宇说彼时“全国最发达之金融机关则为典当业”。
又据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典业公所公议章程十则碑》称:“上海典铺,星罗棋布,已遍城乡。倘再有新创之典,必须同业集议。”可知其时上海已建有典业公所的行业组织。
任何行业,没有节制过滥发展,必然会带来负效应,典当业亦然,毕竟其中有不菲的利润可赚。至于赚头有多少,从黄仁宇将高利贷和典当业相联系,颇可见出一斑。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说,“因高利贷有如典当业,通常盘剥穷蹙之借贷者,借款用于窘迫间之消耗,利润又多为放款者辗转购置田产,对促进商业,绝鲜功效”。
上世纪30年代末,曾出现在上海《中华日报》上的一则报道报道得可要透彻详尽多了——
“据本市典当业方面消息:值此百物昂贵,民不聊生之秋,本市典当营业,非但未见繁荣,反日趋冷淡。查战前本市中区较大同业,日常架本,常在三十万元左右。自去年下半年起,均不过十余万元。……当局方面,较贵重之金银珠宝,早经由所有者,转辗销售于暴富户中,不再重入典门,珍贵皮货亦然,其余不甚值钱之衣服,既非典当所欢迎,同时所得细微之钱,实不足供一人一日食宿之需,此皆押店交易,与典当业无关。至满期当品,更无不赎去,即无力赎取者,亦必出售当票,由他人代赎。最近沪市不乏专营此项业务者,去年均获巨利,此当业”架本“日趋减少之一种主要原因。至押店营业,亦并不见佳,新春以来,尤感清淡,洵属今日沪市民生恐慌声中之一种矛盾状态,足供研究。惟西区一带,押店营业近来异常发达,此系专恃一般赌徒,作孤注一掷之需,无关平民日常生活上救济用途也。”所以为了抑制它的盲目发展,不得不采取一些制约措施。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1932—1933年)记载,上海在1932年时有典铺40家,当铺43家,押店84家和质店5家。这里将典、当、押、质等予以区分是很明显的。如此区分见之于近人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是书“农商类·典质业”云:“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曰押。典、质之性质相等,赎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这样的区分后来亦为治典当学的学人所接受。如著《中国典当业》的杨肇遇、著《典当论》的宓公干等。尤其是前者,我觉得他在这样的区分中更是作出了自己的学术分析。我相信他所作的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近现代典当业的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典当种类之分别,虽无一定明文可考,但据老于斯业者云,典、当、质、押四者之间,亦稍有数点可分,固非仅就资本大小为标准也。如云典者,今几与当混称,实则典为最大。在昔凡称为典者,其质物之额,并无限制。譬如有人以连城之璧,而质万千,其值固不止万千,则典铺决不能以财力不及,拒而不受。当铺则可以不受,盖当铺对于质贷之额,可有限也。逾其额限之数,虽值过数倍,当铺可婉辞而却质,此典与当之分别一也。典铺之柜台,必为一字形,而当铺应作曲尺形,盖典只有直柜,不设横柜,当则直柜与横柜并设,此典与当之分别二也。前清末叶,闻可称为典者,尚有二铺,一在北京,一在南京,后皆因故自行收歇,以后典遂不存,当亦称典,质贷之额,固不能无限制,直柜横柜,更无定制,一以视财力之厚薄,而自为伸缩。一以视装修之便否,而定设备。故典与当,不特名词之混称,而实质上亦难以区别矣。至取利之高下,期限之长短,亦可稍示区别。如汉镇昔年二分取息,二十个月满当者,即称典。其余取息稍重,期限稍短,即称当。此因区域不同,而典当二者之分,亦稍异其旨也。
“至质与押,则其规模视当犹小,当质之分,大抵在纳税上,如苏省当之领帖,需纳帖费五百元,质则只需三百元,押则只需一百元。其他地方公益慈善等捐,质押亦视典当为小。至押犹小于质,其期限极短,不过数月,其利息极重,多三分九扣。……是就原始之典当质押四者而言,则典之资本最大,期限最长,利息最轻,押值亦较高。当次之,质又次之,押则适得其反耳。……故我国之典当业,虽有典当质押四种名称,第因时代之迁延,地域之睽隔,而欲严为区(分),盖亦难矣。”
不管是分四种还是分五种,我想这段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典当业发展的历史,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小时候曾不止一次听到长辈们讲旧上海的典当行是“穷人的后门”这句话。一位邻居大爷更有声有色地对我讲述道,“我年轻时跑过典当行,当时家里急着等钱用,一时又缺钱,怎么办,只能去当铺当东西。那次我是去当衣服。我人矮,站在高高的当铺柜台前,只能使劲踮起脚将衣服递给里面的朝奉先生。面孔冷冰冰的朝奉先生接过我递上的衣服,粗粗看了看,然后问我,‘当几佃?’我回答说,‘五块。’朝奉先生说,‘五元不成。我本来只能当给你三块的,这样吧,四块,成你就放下,不成你拿东西走人。’家里等着用钱,四块就四块吧。我知道再不知趣回嘴,朝奉先生就会别转脑袋不睬我了”。
邻居大爷接下来告诉我,朝奉先生的面孔并不总是冷冰冰的,遇到大票头的当户去当赤金和贵重皮毛货,前者立马就会换上一副和颜悦色的神情,问起话来也会客气许多。经历过旧上海“当铺之辱”的邻居大爷说到这里不由愤然道,“这就是旧上海当铺的势利眼!”
郁慕侠《上海鳞爪》一书中有一则“跑老虎当”的记载,在我看来,此类故事的发生,作案者瞅准的还正是“旧上海当铺的势利眼”——
“市面上靠跑老虎当混饭的人也有好几百,他们的目的专向旧货摊上、各小押店收买各种衣服首饰、珠钻宝石。买来后,改造一次,修饰一回,然后分遣徒党到各大典当去当钱,朝奉先生偶然失察,就要吃他们的亏。譬如有一样东西卖价只值五块钱,进了典当反当了六七块,这岂不是当价超过于卖价么?
“他们当了以后,还将质券交于同行(即出卖质券人),又可增加一些进账。贪便宜辈买了质券,加利去赎出,这个亏就移到贪便宜的身上。但是一经赎出,瞧着不对,乃要照原价当进去,那朝奉先生已不能奉命了。
“到了现在,西洋镜已经拆穿,当里的朝奉很不易受愚,贪便宜买质券的人也愈弄愈少,因此跑老虎当者收进易,脱手难,故混这碗饭的人目下已不如从前的多了。”
在“混这碗饭的人”中虽不乏“旧上海当铺的势利眼”的反叛者,但更多的是一些市井无赖、社会渣滓,他们往往瞄准一些违规操作的小押铺,作为他们生财有道的一大途径。《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七》记载,嘉庆八年(1803年)时,北京城即有专取赃物的小押铺。这些小押铺,“不过希图谋利,而鼠窃匪徒,藉以销赃。并闻各街市,于天尚未明时,即摆摊售卖,最为藏奸。而售主亦贪图便宜,即明知实系贼赃,亦不查询来历,殊非日中为市之义。此时若将小押角概行查禁,在彼生理微薄者,或不免失业无依。若不示以例禁,则奸宄公然售卖赃物,尚复何所顾忌。嗣后著步军统领衙门及五城出示晓谕,不得仍前开设小押,其在街市摆摊者,总于日出后方准售卖。倘其中有来历不明之物,于犯案后查出,即将知情售卖之人按律治罪”。
当铺的违规还不仅于此。且让我们仍然将探究的视野转向旧上海。从一些岁入迟暮的“老上海”口中,我还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旧上海的回力球场曾是个大赌场。赌客参赌一旦输光了身上的钱,可以到就近的当铺去拿随身带着的东西当钱再赌。一些典当商瞅准了这一点,遂纷纷在回力球场周围开设了益源、久丰等大小典当行。为了拉生意,一些典当商还给典当行周边代赌客典当的茶役以回佣和小费。赌场内衣帽间的头目自然也不肯放过赚钱机会,他们索性凑分子直接在场内受理输了钱的赌客的典当,他们给予对方的赎当期限仅为当天。过了这个期限不来赎当,他们就将当物送进典当行,常常就此获利。
2002年5月10日上海《新闻晚报》曾报道,典当行业主管部门——国家经贸委在暂停审批六年后,重新审批了114家新的典当行,从而使全国的典当公司达到了1004家。
物是人非,典当在今天早已是脱胎换骨了。诚如有媒体道出的,典当公司已日益成为上海人身边新的融资窗口和中小企业融资的绿色通道。典当业务除了金银首饰和手表,更有房地产、机动车、生产资料等等。有意思的是,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老典当居然遇上了新难题——一些老外走进了典当行!
走进典当行的老外或亮出手里的新款手表,或递上高配置的手提电脑,或带来崭新的数码相机,然后用蹩脚的汉语问道:“请问,这能当多少钱?”
典当行的估价师犯难了,他确实吃不准这些东西该当多少钱。
曾有一位朋友和我讲起这样一件事:有位俄罗斯人到华联典当行典当一款2000年的伯爵表。估价师脸上露出一脸为难:伯爵表排名世界前十位,它的名贵不言而喻,但到底该当多少钱,他一时也很难判断到位。
新的问题出现的同时,也是新的商机存在的写照。所以,我们有理由为之感到欣慰。
今天,历史已经进入了新世纪。昔日的典当行已经远了。走近我们的已然是全新意义上的典当业。据此前沪上一家报纸报道,全国规模最大的典当行在沪开张,宣称汽车、房产皆可质钱,还将从事股票质押贷款。果然,这样的典当行开张后,一些投资者、生意人、房产商看中其比银行更便捷的时效,纷纷向它“调头寸”,把资产转化为资金用于再投资。以至有识者指出,以前一直是“穷人的后门”的当铺,如今已然成了一个特殊的金融机构。但是尽管如此,看到那个硕大的繁体“当”字,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已经远去的老上海当铺。尤其是当我在梳理有关旧上海社会舞台上曾经出现的一幕幕场景时,那个触目惊心的繁体“当”字更是时时回闪在眼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记述他对旧上海的印象时说,“上海虽为世界第一流的城市,在墙壁上以丈尺大字写出的商业标识不是雪佛兰轿车或奇异GE电气用品,而是当铺之‘当’与酱园之‘酱’。”在我看来,这个“当”字分明也是历史对现实的一种提醒,提醒今天,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幕。
好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全家曾去已故著名作家茅盾的家乡桐乡乌镇旅游,当时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的陆泱在旅游参观景点之一的乌镇老当铺时,居然足足逗留了老半天,他一会儿坐上高高的典当柜后面那把高凳,目光透过眼前那扇小窗,望着游人出出进进;一会儿又跳下来,颇感新鲜地在八仙桌旁的大扶手椅上坐坐,我猜测儿子对这里的印象一定觉得非常好玩。他对历史的阅读和了解还很有限,还体会不到那时的穷人挟着典当物战战兢兢走近当铺,会是一种什么心境;还不懂得探究在这些前来当铺的穷人家里正发生着什么。
近代上海的典当业是相当兴盛的。说中国典当业的存在已有几千年历史决不为过。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曾引述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中的记载说,16世纪中国有当铺两万家,至19世纪仍有七千家,所以黄仁宇说彼时“全国最发达之金融机关则为典当业”。
又据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典业公所公议章程十则碑》称:“上海典铺,星罗棋布,已遍城乡。倘再有新创之典,必须同业集议。”可知其时上海已建有典业公所的行业组织。
任何行业,没有节制过滥发展,必然会带来负效应,典当业亦然,毕竟其中有不菲的利润可赚。至于赚头有多少,从黄仁宇将高利贷和典当业相联系,颇可见出一斑。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说,“因高利贷有如典当业,通常盘剥穷蹙之借贷者,借款用于窘迫间之消耗,利润又多为放款者辗转购置田产,对促进商业,绝鲜功效”。
上世纪30年代末,曾出现在上海《中华日报》上的一则报道报道得可要透彻详尽多了——
“据本市典当业方面消息:值此百物昂贵,民不聊生之秋,本市典当营业,非但未见繁荣,反日趋冷淡。查战前本市中区较大同业,日常架本,常在三十万元左右。自去年下半年起,均不过十余万元。……当局方面,较贵重之金银珠宝,早经由所有者,转辗销售于暴富户中,不再重入典门,珍贵皮货亦然,其余不甚值钱之衣服,既非典当所欢迎,同时所得细微之钱,实不足供一人一日食宿之需,此皆押店交易,与典当业无关。至满期当品,更无不赎去,即无力赎取者,亦必出售当票,由他人代赎。最近沪市不乏专营此项业务者,去年均获巨利,此当业”架本“日趋减少之一种主要原因。至押店营业,亦并不见佳,新春以来,尤感清淡,洵属今日沪市民生恐慌声中之一种矛盾状态,足供研究。惟西区一带,押店营业近来异常发达,此系专恃一般赌徒,作孤注一掷之需,无关平民日常生活上救济用途也。”所以为了抑制它的盲目发展,不得不采取一些制约措施。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1932—1933年)记载,上海在1932年时有典铺40家,当铺43家,押店84家和质店5家。这里将典、当、押、质等予以区分是很明显的。如此区分见之于近人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是书“农商类·典质业”云:“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曰押。典、质之性质相等,赎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这样的区分后来亦为治典当学的学人所接受。如著《中国典当业》的杨肇遇、著《典当论》的宓公干等。尤其是前者,我觉得他在这样的区分中更是作出了自己的学术分析。我相信他所作的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近现代典当业的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典当种类之分别,虽无一定明文可考,但据老于斯业者云,典、当、质、押四者之间,亦稍有数点可分,固非仅就资本大小为标准也。如云典者,今几与当混称,实则典为最大。在昔凡称为典者,其质物之额,并无限制。譬如有人以连城之璧,而质万千,其值固不止万千,则典铺决不能以财力不及,拒而不受。当铺则可以不受,盖当铺对于质贷之额,可有限也。逾其额限之数,虽值过数倍,当铺可婉辞而却质,此典与当之分别一也。典铺之柜台,必为一字形,而当铺应作曲尺形,盖典只有直柜,不设横柜,当则直柜与横柜并设,此典与当之分别二也。前清末叶,闻可称为典者,尚有二铺,一在北京,一在南京,后皆因故自行收歇,以后典遂不存,当亦称典,质贷之额,固不能无限制,直柜横柜,更无定制,一以视财力之厚薄,而自为伸缩。一以视装修之便否,而定设备。故典与当,不特名词之混称,而实质上亦难以区别矣。至取利之高下,期限之长短,亦可稍示区别。如汉镇昔年二分取息,二十个月满当者,即称典。其余取息稍重,期限稍短,即称当。此因区域不同,而典当二者之分,亦稍异其旨也。
“至质与押,则其规模视当犹小,当质之分,大抵在纳税上,如苏省当之领帖,需纳帖费五百元,质则只需三百元,押则只需一百元。其他地方公益慈善等捐,质押亦视典当为小。至押犹小于质,其期限极短,不过数月,其利息极重,多三分九扣。……是就原始之典当质押四者而言,则典之资本最大,期限最长,利息最轻,押值亦较高。当次之,质又次之,押则适得其反耳。……故我国之典当业,虽有典当质押四种名称,第因时代之迁延,地域之睽隔,而欲严为区(分),盖亦难矣。”
不管是分四种还是分五种,我想这段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典当业发展的历史,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小时候曾不止一次听到长辈们讲旧上海的典当行是“穷人的后门”这句话。一位邻居大爷更有声有色地对我讲述道,“我年轻时跑过典当行,当时家里急着等钱用,一时又缺钱,怎么办,只能去当铺当东西。那次我是去当衣服。我人矮,站在高高的当铺柜台前,只能使劲踮起脚将衣服递给里面的朝奉先生。面孔冷冰冰的朝奉先生接过我递上的衣服,粗粗看了看,然后问我,‘当几佃?’我回答说,‘五块。’朝奉先生说,‘五元不成。我本来只能当给你三块的,这样吧,四块,成你就放下,不成你拿东西走人。’家里等着用钱,四块就四块吧。我知道再不知趣回嘴,朝奉先生就会别转脑袋不睬我了”。
邻居大爷接下来告诉我,朝奉先生的面孔并不总是冷冰冰的,遇到大票头的当户去当赤金和贵重皮毛货,前者立马就会换上一副和颜悦色的神情,问起话来也会客气许多。经历过旧上海“当铺之辱”的邻居大爷说到这里不由愤然道,“这就是旧上海当铺的势利眼!”
郁慕侠《上海鳞爪》一书中有一则“跑老虎当”的记载,在我看来,此类故事的发生,作案者瞅准的还正是“旧上海当铺的势利眼”——
“市面上靠跑老虎当混饭的人也有好几百,他们的目的专向旧货摊上、各小押店收买各种衣服首饰、珠钻宝石。买来后,改造一次,修饰一回,然后分遣徒党到各大典当去当钱,朝奉先生偶然失察,就要吃他们的亏。譬如有一样东西卖价只值五块钱,进了典当反当了六七块,这岂不是当价超过于卖价么?
“他们当了以后,还将质券交于同行(即出卖质券人),又可增加一些进账。贪便宜辈买了质券,加利去赎出,这个亏就移到贪便宜的身上。但是一经赎出,瞧着不对,乃要照原价当进去,那朝奉先生已不能奉命了。
“到了现在,西洋镜已经拆穿,当里的朝奉很不易受愚,贪便宜买质券的人也愈弄愈少,因此跑老虎当者收进易,脱手难,故混这碗饭的人目下已不如从前的多了。”
在“混这碗饭的人”中虽不乏“旧上海当铺的势利眼”的反叛者,但更多的是一些市井无赖、社会渣滓,他们往往瞄准一些违规操作的小押铺,作为他们生财有道的一大途径。《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七》记载,嘉庆八年(1803年)时,北京城即有专取赃物的小押铺。这些小押铺,“不过希图谋利,而鼠窃匪徒,藉以销赃。并闻各街市,于天尚未明时,即摆摊售卖,最为藏奸。而售主亦贪图便宜,即明知实系贼赃,亦不查询来历,殊非日中为市之义。此时若将小押角概行查禁,在彼生理微薄者,或不免失业无依。若不示以例禁,则奸宄公然售卖赃物,尚复何所顾忌。嗣后著步军统领衙门及五城出示晓谕,不得仍前开设小押,其在街市摆摊者,总于日出后方准售卖。倘其中有来历不明之物,于犯案后查出,即将知情售卖之人按律治罪”。
当铺的违规还不仅于此。且让我们仍然将探究的视野转向旧上海。从一些岁入迟暮的“老上海”口中,我还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旧上海的回力球场曾是个大赌场。赌客参赌一旦输光了身上的钱,可以到就近的当铺去拿随身带着的东西当钱再赌。一些典当商瞅准了这一点,遂纷纷在回力球场周围开设了益源、久丰等大小典当行。为了拉生意,一些典当商还给典当行周边代赌客典当的茶役以回佣和小费。赌场内衣帽间的头目自然也不肯放过赚钱机会,他们索性凑分子直接在场内受理输了钱的赌客的典当,他们给予对方的赎当期限仅为当天。过了这个期限不来赎当,他们就将当物送进典当行,常常就此获利。
2002年5月10日上海《新闻晚报》曾报道,典当行业主管部门——国家经贸委在暂停审批六年后,重新审批了114家新的典当行,从而使全国的典当公司达到了1004家。
物是人非,典当在今天早已是脱胎换骨了。诚如有媒体道出的,典当公司已日益成为上海人身边新的融资窗口和中小企业融资的绿色通道。典当业务除了金银首饰和手表,更有房地产、机动车、生产资料等等。有意思的是,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老典当居然遇上了新难题——一些老外走进了典当行!
走进典当行的老外或亮出手里的新款手表,或递上高配置的手提电脑,或带来崭新的数码相机,然后用蹩脚的汉语问道:“请问,这能当多少钱?”
典当行的估价师犯难了,他确实吃不准这些东西该当多少钱。
曾有一位朋友和我讲起这样一件事:有位俄罗斯人到华联典当行典当一款2000年的伯爵表。估价师脸上露出一脸为难:伯爵表排名世界前十位,它的名贵不言而喻,但到底该当多少钱,他一时也很难判断到位。
新的问题出现的同时,也是新的商机存在的写照。所以,我们有理由为之感到欣慰。
- 上一篇:上海典当行细说中国典权制度的变迁 2014/7/14
- 下一篇:上海企业动产抵押典当物登记管理办法 2014/7/14